小剧场话剧如何赢得更多掌声?
2025-02-14 发表|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刘万赟今年春节期间,国人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娱乐选择。当人们走出家门,在电影院、剧院齐聚的同时,很多观众也将目光投向了小剧场演出。如被誉为小剧场“神作”的《未完待续》尽管问世近20年,但于近期在北京人艺菊隐剧场三天四场的演出,现场仍旧座无虚席。对于很多年轻人,到小剧场“打卡”“刷剧”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国内小剧场话剧演出的独特生态与文化现象,已经有力推动了戏剧艺术市场的下沉和拓展。

中国话剧的奠基人、著名剧作家曹禺曾经说:“小剧场是创造高度戏剧文明的园地。”“小而精”“实验性”是小剧场话剧最为突出的风格特征。无论是剧场空间、演出时长、制作成本、演员规模,还是作品题材、情节结构、舞台调度、舞美布景,小剧场话剧都鲜明地体现着有别于大剧场演出的特色优势。小剧场的观众同演员的空间距离较近、情感联结紧密,像传统镜框式舞台那般的“第四堵墙”不复存在,极易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体验感、参与感和互动感,有助于更加全面且深刻地传达创作者的思想表意与剧作主题。对编剧、导演们来说,小剧场也往往蕴藏着更大的包容性和探索性空间。创作者对于现实生活的洞察及对于艺术形象的雕琢,能够在更加自由的园地里奔突驰骋,愈发靠近生命、情感、人性、哲学等重大命题……探索品格和创新精神也因此成为了小剧场话剧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进入新时代,小剧场话剧迎来了更多、更新的发展机遇。伴随着审美思潮的演变,观众对小剧场话剧在类型数量和作品质量方面所持的期待与要求越来越高。从2012年“首届北京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到2017年“全国小剧场戏剧优秀剧目展演”,再到2023年“首届全国小剧场戏剧‘紫金杯’优秀剧目展演”、2024年中国剧协“第二届全国小剧场戏剧优秀剧目展演”……各级有关单位为有效推动、引导小剧场话剧的剧目创作和良性发展搭建了广阔平台;同时,基于文化政策的积极扶持,国家艺术基金及各地艺术创作基金也多为小剧场话剧增设专项,并不断着力提升小剧场话剧艺术在文旅融合开发过程中的动态势能与产业价值。在国家和政府层面的正向引领下,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民营社团和演出机构也进一步参与到小剧场话剧的孵化与制作中来,如哲腾文化、木马剧社、黄盈工作室、李伯男戏剧工作室……充分激发了小剧场话剧演出市场的活力,共同构建起中国当代戏剧创演的新生态和新图景。
然而,在热闹的景象之下,我们也应该看到,不少观众的期望值却同实际观演体验产生了错位,不少创作者的灵感、热情也逐日趋于冷却。小剧场话剧的“先锋性”“探索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商业性的过分袭扰,随着演出市场的扩大,一些问题慢慢暴露出来:
首先,从目前流行的题材类型上看,悬疑、喜剧类作品比较受小剧场话剧投资人及制作团队的青睐。但悬疑作品多基于对已形成固定粉丝群体的小说进行IP改编与舞台转化,依赖性强、原创乏力;喜剧作品虽剔除了早先的低俗内容,却又难以在人物个性、情境要素上充分开掘喜剧因子,导致喜剧性仅浮于语言表层、流于动作形式,创作者出于同观众交流互动所进行的“融梗”、所设计的“包袱”有时显得简单生硬、缺少层次,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因此,为避免陷入题材单一的泥淖,创作者应敢于挑战“类型化”这块铁板,勇于尝试和创新,有意识地拓展题材边界、丰富作品类型。
其次,从创作周期和流程来说,有些小剧场话剧在剧本尚未成熟之前就急于推进选角、宣发等工作,乃至同剧场方面明确了演出时间。这样一来,留给创作者尤其是编剧的时间便极为有限,作品打磨、修改不够细致,内容深度及人物形象丰满程度欠缺,甚或存在严重的逻辑漏洞,出现后续剧本围读和排演都难以补救的“硬伤”……这种质量粗糙的“急就章”之作,很难获得观众的肯定与市场的认可。
再次,就部分小剧场话剧的巡演与大剧场版本的推出而言,也存在着“边改边演”“只演不改”的问题——“边改边演”,主要针对一些作品的巡演来说,即在巡演过程中对演出内容不断修正、调整,虽看似有着“自我革新”“自我批评”的精神品质,从另一面来说却也是对观众的不负责任,将修改的空间放在了演出过程中,问题根源还是在于前期创排工作;“只演不改”,则是一些小剧场话剧在后期演出大剧场版本时的“通病”,导演或疏忽剧场观演距离、舞台空间大小之不同,或惰于重新排演,在人物关系、线索结构等内容上和场面调度、技术手段等形式上,仍保留着小剧场版本的设计安排,致使作品同舞台空间无法保持有机融合,亦影响观众的审美体验。
最后,关于小剧场话剧演出空间选择及舞台设计的问题,仍想补充和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场地的随意性,如果说露天小舞台尚可视为对正规小剧场的灵活补充、映衬,那么在餐厅、酒吧的演出便不免被厚厚蒙上一层娱乐性、商业性的烟尘,深邃、严肃的戏剧主题往往跟欢娱、轻松的环境氛围南辕北辙;二是舞美的简单化,小剧场话剧的“小”并不意味着要对置景、灯光、道具、音效等舞台元素进行极限压缩,把小剧场话剧做成“穷干戏剧”,应当在有限的空间和条件下,盘活各种技术手段并为作品所用,方能达成“小而美”“美而精”“精而深”的艺术追求。
前路关隘虽多,却也风光无限。依托未来更多的基金与孵化项目,小剧场话剧从业者也将获得更加有力的政策扶持,创作出更加精湛的艺术作品。深思、深耕、深远,更需夯实文本架构基础、强化舞台表现手段,进一步开掘民族题材资源、转化民族经典母本、传播民族风格话语、塑造民族演剧体系、提升民族艺术审美、担当民族文化重任,积极助力中国小剧场话剧迈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赢得更多国内外戏剧观众的首肯和掌声。









 “群星璀璨”2025新春山西省群众文化优秀
“群星璀璨”2025新春山西省群众文化优秀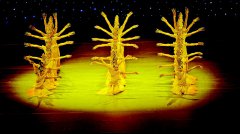 舞剧《千手观音》忻州精彩上演
舞剧《千手观音》忻州精彩上演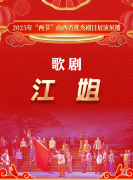 歌剧《江姐》2月15日至16日山西大剧院上
歌剧《江姐》2月15日至16日山西大剧院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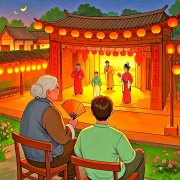 陪岳母看戏
陪岳母看戏 小剧场话剧如何赢得更多掌声?
小剧场话剧如何赢得更多掌声?

 晋公网安备14010902001572
晋公网安备140109020015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