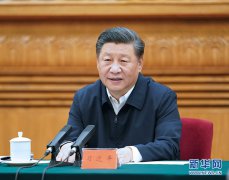万方:父亲曹禺的爱与真诚
2020-09-23 发表|来源:文汇报|作者:彭丹



今年9月24日是著名戏剧家曹禺先生诞辰110周年。前不久,曹禺的女儿——同为剧作家的万方出版了长篇非虚构作品《你和我》追忆自己的父母。书里展现了一个在戏剧大师光环之下,作为普通人、更有血有肉的曹禺——他对爱情的执着大胆、对女儿的舐犊情深、幼年爬上城垛听军营号声时的孤独、写作时的痴迷、从衣服里抖落出老鼠的窘相还有晚年写不出作品时的痛苦等。
万方像抽丝剥茧的侦探般爬梳着过往,又以作家开掘复杂人性的敏锐、越过狭隘道德的包容去理解自己的父亲、母亲以及父母周围的那些人们,理解他们的情感与命运。对她来说,这不仅是一趟艰难的回溯之旅,也是自我认知之旅。正如她在书中所说:“我写这本书不是想介绍一位剧作家,我要写的是我的爸爸和妈妈,我要细细探索,好好地认识他们,还想通过他们认清我自己。”
出生于1952年的万方,常被曹禺说是4个女儿里最像自己的。上世纪80年代初,她也走上了文学道路,作品跨越中长篇小说、影视剧本、话剧等,其中许多聚焦于女性独有的生命律动与复杂、精细、隐秘的感情世界。她编剧的《空镜子》《你是苹果我是梨》等影视剧深受观众喜爱。她曾将曹禺的话剧《日出》改编为电影,获得了当年的金鸡奖最佳编剧奖。
54岁那年,万方首次写作的话剧《有一种毒药》获得了第2届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这次写作《你和我》,她说自己最大的追求是真实。妹妹对她说:“你所知道的根本不是真相,只是一些碎珠子。”万方坚持认为,即便不完整,也必须在碎珠子中寻找,“真相就存在于寻找之中,寻找的行为本身也是一种真实。”
对真实的深入挖掘,使得《你和我》不光成了万方“与父母及其周围生命的一场对话”,那些越是细如毫发的感受,越具有潜入每个读者境遇的可能,它启示每个人去思考真实的自我,于是《你和我》中是“你”也是“我”。
创作新书是为了贴近父亲母亲的生命
万方创作《你和我》,缘起于父母间的一沓书信。1940年代,四川江安县,曹禺任国立剧专的教导主任。在这个长江边上的小城,他遇见了名门闺秀邓译生(又名方瑞)并对她一见钟情,虽然那时他尚有家室。
邓译生的曾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她从小学诗作画。两人的爱情在一封封炽热的情书间流淌,曹禺以恋人为原型写作了《北京人》里的 “愫方”, “愫” 取作邓译生母亲的名字“方愫悌”,“方”取自曹禺为邓译生取的“方瑞”一名。后来不少评论者认为《北京人》是曹禺的顶尖之作,它也是万方最喜欢的父亲的一部作品。
1996年曹禺去世后,万方的继母李玉茹把曹禺与方瑞间的所有通信都交给了万方,“薄若蝉翼的纸张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蚂蚁般的小字”,字迹已经变淡。万方仔细辨认每一个字,把它们打入电脑里,她震撼于父母浓烈、真挚的爱情,更让她惊讶的是文弱、温婉的母亲曾经为了爱情如此强大、勇敢,记忆中受了很多苦的她原来也有过旁人难比的幸福。
1974年母亲因服用过量安眠药意外去世时,万方才二十岁出头,多年来她仍经常梦见母亲,难过当初母亲说手疼却不懂得为她捏捏手。随着年岁越来越大,她想要为母亲 “做点什么”的渴望也愈发强烈,这些信像“一道灿烂的光照亮了自己的生命”。作为写作者,她能做的就是把这道光从起念到落笔,万方挣扎了10年之久。在以往的采访中,她总是避谈父母间的事,如今要把它们一一摊开,她不得不顾忌社会上的道德成见,也要克服极大的心理障碍,去正视那些埋藏在心里多年的隐疾,以及势不可挡的阴影。在最初酝酿勇气开始写作的两三个月,她因情绪激动,血压一下子飙升到了170多。
“所幸,在写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心理上一点点发生了变化,变得不再那么踌躇多虑,更趋于坦然,坦然地面对真相。”写书之前,万方就坚定,“我必须真实,如果不真实我就不写。”她慢慢看透写作是什么、活着是什么,而能不能写出这本真实的书关乎到上述问题的答案。
万方觉得,写作不是要去迎合大众心中对文学巨匠的完美想象,也不是将事实削足适履嵌套进世俗规范里,而是要写出真实的人与人性,人更是要有一颗自由的心灵。在书中,除了记录温馨的家庭往事,抒发对父母的诚挚思念,她也没有回避人性的种种弱点,直面父母那段颇受争议的婚外恋情、“文革”中所遭受的折磨、父母服用安眠药成瘾的悲剧、父亲晚年再也写不出作品时的痛苦等等。
“有段时间我看到爸爸一小时一小时地趴在客厅方桌上,不停地写、写、写。我手里有张纸,他在纸上写着‘为什么一个字也写不出?’”万方看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父亲,头衔越来越多,整天忙于各种会议、活动,回来时往沙发上一倒,满脸疲倦与沮丧。可他仍会在夜晚叫喊,心有不甘地说要像离家出走的托尔斯泰一样,“放弃这个‘嘴’的生活,用脚踩出我的生活,手写真实的人生。”
只是这些话语都落空了。有人说晚年的曹禺江郎才尽,万方却说父亲不是“才尽”,只是他将外界的条条框框内化成心里的枷锁,开始怀疑自己,根基动摇。一个失去自我的人又如何写出好作品?万方同情父亲,更理解父亲:“爸爸不是一个斗士,也不是思想家,他生性脆弱、极度感性,时刻会被美好自由的感觉所吸引,内心却又悲观,是一个彻头彻尾、如假包换的艺术家。他胆小,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说过许多错话、假话、违心话,但他的心始终真诚。如果只用一个词形容他,这个词就是真诚。”
“我和爸爸的生命,用了很多相同的材料”
从事写作或许是继承了父亲的敏感,也得益于从小受到的熏陶。小时候,万方家住在铁狮子胡同3号(现为张自忠路5号),那时她和院里的小孩在海棠树边跳皮筋,听到书房里的父亲读着他写的台词,那发自内心、“不同凡响”的朗读令她难以忘怀。
幼年时跟父亲去钓鱼,大半个下午只钓上枯树枝和一只鞋,她和父亲编了个“鱼爸爸鱼妈妈”的故事,之所以钓不到鱼是鱼妈妈带着孩子去找鱼爸爸了。父亲给她讲三公主和四公主的故事,三公主缺点多,还欺负四公主,在姐妹中排行老三的万方不高兴了,父亲又在她的强烈抗议下把三公主变好。
1969年,年仅16岁的万方到吉林插队,在农村田头,“常有被风卷起的感觉,有时饿极了便到老乡家要点杂粮与咸菜”,这段插队生活也成了她以后小说里的素材来源之一。1970年,沈阳军区前进歌剧团的政委因崇拜曹禺,“爱屋及乌”把万方招进歌剧团做创作员,“算是入了文字一行”。之后她又离开部队,在《剧本》月刊做编辑,1980年起在中央歌剧院担任编剧。从那时起,她真正开始带有自身风格的文学创作。
因为自身的遭遇,父亲曹禺并不想女儿成为作家,他更想让她们当科学家或者医生。对于女儿的决定,他却从来都予以尊重。“爸爸教给我的是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生命的核:自由的感觉。他从来没有对我用过‘自由’这个词,但在抚育孩子这件事上他是自由的行动派。”
和许多从自身经历出发写作的作家一样,万方最初的作品也都与自己的生活、情感息息相关。她的第一篇小说《星星离我们并不遥远》发表在《收获》杂志上,陆续又写了一两篇小说的她对自己并不满意,甚至一度心灰意冷,直到写出了《杀人》这一中篇小说。它以上世纪50年代的农村为背景,写了一个被道德沉疴戕害了的妇女的故事。小说离她本人很遥远,是她综合了自己观察到的困在婚姻牢笼里的同学妈妈、对城市人羡慕不已的农村女孩和从丈夫那里听到的一桩离奇的傻子 “失踪案”,慢慢将它们“拧”成了一个决绝、触目惊心的故事。
万方把发表《杀人》的那期《收获》杂志故意留在父亲曹禺当时住的医院。第二天父亲一看到她来,眼睛一亮,兴奋地把她拉到身边:“小方子你真行,你还真的能写。”至此万方知道,她“能吃写作这碗饭了”。
或许是出于年轻人的“叛逆”,那时的万方并不想让尊为戏剧大师的父亲来指导自己的写作,她“不想沾父亲的光,我要靠我自己”。然而多年后,再回看父亲写给自己的信,她发现父亲的良苦用心都渗透在字字句句里:
“方子,你不能再玩了。你要观察、体会身边的一切事物、人物,写出他们,完全无误,写出他们的神态、风趣和生动的语言,不断看见、觉察出来,那些崇高的灵魂在文字间怎样闪光……”
“一个作家必须有真正的思想。一个人没有思想便不成其为人,更何况一个作家。其实向往着光明的思想才能使人写出好东西来,你以为如何?希望你能真正在创作中得到平静快乐的心情。”
……
最重要的是,万方继承了父亲身上的敏感,对周遭生活里微妙音色的感受和对大千世界里人的兴趣。她说:“我的爸爸,和我心心相通,我的所有感受他都会懂、会明白,只有他。当看完一出戏,当看着夕阳倏忽退去,当站立月下,我们俩想的一样,感受一样,他和我的生命一定是用了很多相同的材料。”
曹禺晚年住进了北京医院,与医院一路相隔的是东单公园,万方曾陪他去到公园里,父亲津津有味地看着跳交谊舞的人们,还悄悄指给她看“一个油头男人脖子上系着的花围巾”。有一回,万方饭后陪父亲散步,走着走着发现父亲不见了,回头看到他正盯着一对相拥走远的年轻情侣出神,兀自喃喃道:“没有比青春再好的东西了!”
“父亲对人的兴趣已深入骨髓,用他自己的话说:‘人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人又是非常宝贵的,人是多么难以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说我把人说清楚了。’”万方觉得,自己对人、对生活细节的敏感是传承在基因里的,也是受父亲耳濡目染的影响。随着经历的沉淀,这种感受力就像一把越磨越锋利的“刀”,它刺穿平凡生活的表面,扎向混沌的人性深处。
写女性,有受到父亲的影响
万方的笔下,女性是重要的书写对象。她写被如钢丝一样的传统礼教深深束缚的农村妇女、写遭受爱人背叛后走向沉沦的年轻少女、写挣扎在婚姻围城里的女性……万方用自己细腻、宽容的女性视角,去解剖微妙的两性关系、家庭与婚姻,写女性骨子里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她不去评判与说教,只是怀着深切的同理心注视着在情感迷宫里磕磕绊绊、寻寻觅觅的饮食男女——这似乎与父亲曹禺对女性的关怀遥相呼应。
“我对女性的了解与体悟实际上受到了父亲作品的影响。”说起父亲作品中的女性,万方语气激动,“你看他作品中的那些女性人物是非常复杂而又鲜明的。比如‘翠喜’‘繁漪’都会让你感到被紧紧抓住,你的心跟她融在一起。‘繁漪’就是不甘心于自己的命运,现代女性不管在爱情还是工作中,或许潜意识里也有这种不甘的心理。而‘翠喜’那样一个低到泥潭里的人物,身上却散发着一种光芒。我父亲是真正地从女性视角去理解她们的。”
曹禺1910年生于天津的一个官僚家庭,年仅19岁的母亲刚生下他便去世。80岁时,曹禺曾在医院里为母亲写下19页的长诗。万方说:“那是他永远的心疼,这心疼存在于他的每一部剧中,化为无限怜爱,怜爱着他剧中的女性人物。”
“我爸爸爱女人,像干涸的泥土需要水,他需要爱更需要付出爱,《北京人》里的愫方、《雷雨》里的繁漪、《日出》里的陈白露,她们都是他的心尖儿,他珍爱她们、疼她们,多少男人里才有一个会这样地爱女人啊!”曹禺作品里的女性处境与今日已大不一样,但旧观念的阴影或许仍挥之不去,今日女性还面临新困惑。
万方认为,女性的自立至关重要——“我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女人”。她发现如今女性自我意识更强了,但就像她笔下那些人物一样,女性永远在追求真挚爱情的路上。在爱情里,又何尝不是一种人格自由的实现:“女人的了不起就在这个地方,不管她们走了多长的路,穿过多长的岁月,她们的心都不会麻木,对爱情的渴望永远像一团小小的火种,像燧石,有了这块坚硬的磨不完的燧石就有了希望,就能点起火,就能燃烧。”
“写作是向答案一刻不停地靠近”
生活中的万方打扮素净,眼神清澈、从容。她的话带着北京腔特有的爽朗、亲切,就像身边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者。然而把目光转向她的一些作品,里面有激烈的死亡、极致的爱恨,有埋藏在人心褶皱深处的阴暗,有压抑许久后冲决而出的欲望,质地坚硬而深刻。
“我的大部分小说里,有一种挺决绝的东西在里面,这点跟我爸爸挺像的。”万方说,“爸爸的作品里有很深、很尖锐、像刀子一样刺痛人心的东西。我写东西也总有这样一种冲动,想对人性扎得更深一些。”对人性的深度追问也延续在万方的戏剧作品中。虽然小说、影视剧作品早已有了成就,但她直到54岁那年才涉足戏剧,写出了话剧《有一种毒药》。
此前,万方一直不觉得父亲的戏剧成就对自己是压力。直到2006年,《有一种毒药》在上演过父亲无数作品的首都剧场演出时,她忽然意识到,之所以这么晚才动笔写话剧,是因为父亲的“那几部戏剧在压着自己”。它们就像是一座高山,只有等到积累了足够的写作经验,对“语言、结构、人物有了足够的塑造能力”,万方才敢去“够”这座山。
在万方的记忆里,自己最早接触的话剧是父亲的《雷雨》。大概只有三四岁的年纪,她听到《雷雨》第三幕四凤发毒誓后那震动全场的一声响雷,“哇”地一声吓哭了。曹禺伸手把她一把抄起,抱到剧院明亮的侧厅,等她慢慢止住抽泣。“这是关于戏剧我上的第一堂课:剧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后来,万方常跟着父亲去人艺的首都剧场,穿梭在台前与幕后。她看到《雷雨》中“霹雳是悬在高高吊杆上的洋铁板,雷声是鼓,雨声是缀满一颗颗小珠子的大芭蕉扇”;演员如何像“变魔术”一样创造角色;排练厅里走路都得蹑手蹑脚,“让人肃然起敬的气氛”……等到从旁观者变为戏剧人,万方感叹,“是爸爸让我在首都剧场的母体中再次出生,从此开始吸收戏剧的养分。”
写作《有一种毒药》后,万方还创作了《关系》《冬之旅》《新原野》《雷雨·后》等话剧作品。正如在《有一种毒药》中写理想与物质现实的抵牾,《冬之旅》里写遗忘与宽恕伤害的两难,她许多时候都在作品里描写了生活的纠结地带,无法落入是非框架里的价值迷思。
“人,人生,从来都不是清清楚楚的,不可能清清楚楚。困惑、歧义、悖论、不可知、失控随处可见。写戏是因为心中困惑,是想寻求答案。答案也许永远找不到,但写作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向答案靠近的过程。”万方说,生活中的很多问题不像打官司,能有绝对的定论、清晰的判定,实际上,她能做的是“对人类的境遇、人类的天性,做出尽可能生动的反映”,也在写作过程中与观众一道,依据自身的生活经验找寻着答案。
万方坦言,写作已经成为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是不写,可能就会像一片浮萍,不知道漂哪里去了”。写作《你和我》时,她感到像“把流淌过去的东西一点点找回来,好像重活了一遍。”写完此书,她几乎将自己的心血掏空,但也获得了更多的“定力”。
现在,万方在为自己的“乖乖”写一本书。“乖乖”是她在丈夫患病去世后养的小狗,在她最孤独的时候给予了陪伴,教会了她很多东西。《你和我》中也常常见到“乖乖”的身影。今年1月9号,16岁零4个月的“乖乖”离开了。万方一度伤心地搁下了笔,直到逛公园与人聊天意外领养到一条小小的比熊犬,她才又捡起已写了几万字的关于“乖乖”的书。
“看来这条比熊犬又会是一条幸福的小狗。”
“是的,很幸福。”万方回答道。







 现代晋剧《武汉鼎》在鄂尔多斯大剧院上
现代晋剧《武汉鼎》在鄂尔多斯大剧院上 抗战话剧:烽火岁月里的战斗
抗战话剧:烽火岁月里的战斗 2020年晋中市晋剧艺术展演季书画作品展闭
2020年晋中市晋剧艺术展演季书画作品展闭 连台戏纪念曹禺诞辰110周年
连台戏纪念曹禺诞辰110周年 晋中市2016至2020年新编新创优秀剧目首场
晋中市2016至2020年新编新创优秀剧目首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