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生活本身——当代艺术哲学的使命
2017-01-30 发表|来源:上海观察|作者:孙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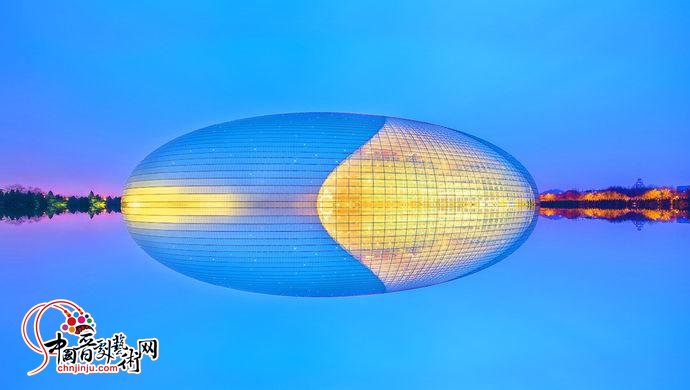
在这个时代,大概没有人再会怀疑艺术对于我们生活的重要意义,因为,正如我们每天所感受到的那样,艺术已经无所不在地融入了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这样一来,有一个问题变得至关重要了,这就是,当代艺术的使命与担当是什么?如果不弄清楚这个问题,那么或者生活将被不负责任的艺术所败坏,或者艺术将被不负责任的生活所败坏。
坦率地说,这并不是一个没有引起人们关注的问题。但是,如果不对关注本身加以检视,那么问题反而会由于关注而变得似是而非。事实上,我们正是发现,这个问题在许多场合有意无意地变成了关于艺术的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的争论。一些专业人士出于并凭借他们的知识训练,往往试图把当代艺术中审美的方面同娱乐的、装饰的方面区分出来,并给予前者以更为重要的意义。这在很多时候被看作是对当代艺术的使命与担当的一种严肃而认真的思考。然而,悖谬的是,那些供奉在博物馆和美术馆中被认为有审美意味的作品,恰恰由于这种遥远的供奉而失去了对于人们生活的意义。反过来,娱乐的、装饰的东西由于给人们带来即时的快乐而成为生活中极为切近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除了帮助人们打发无聊之外,似乎并没有留下别的什么东西,当然,有可能留下了新的无聊。
这一令人难堪的窘境,逼迫我们去重新检视这种审美价值与娱乐价值的前提。我们发现,如果说价值意味着有某种东西可供兑现,那么,艺术的意义就在于给出可供审美或可供娱乐的事情或物件。可是,事实是这样吗?历史的追溯看起来为这个问题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我们知道,今天所谓的艺术基本上是指美的艺术(fine art),主要包括绘画、雕刻、建筑、音乐、诗歌以及戏剧、舞蹈,乃至电影之类。但是在古代,艺术,即希腊人说的τέχυη或罗马人说的ars,有着比今天更为宽泛的意思,它指做某样事情或制某样物件所需要的技能,比如率军作战或者制作一把陶壶所需要的技能。如果我们把这考虑为是对艺术本性的揭示的话,那么我们似乎的确可以说,艺术所给出的就是有什么可供兑现的事情或物件。
比如,既然艺术是做某事的技能,那么由作战的艺术而来的当然就是作战这件事情本身。然而,情况恐怕并非如此,至少杜威认为并非如此,他说:“人们不止是作战,他们是为他们的国家而战。抽象的科学不能传达爱和忠诚……学习作战艺术的方法乃是通过同那些已经学会保卫国家的人结伴,依靠渗透这门艺术的理想和习惯;简而言之,依靠在实际上熟谙希腊人的作战传统。”在这里,显然,作战这门艺术并非像人们以为的那么简单。这是因为,在希腊人那里,作战艺术并不意味着做一件仅仅被认作是作战的事情。相反地,我们从中所看到的是国家、爱、忠诚、理想、习惯、传统等这些在今天看来与作战本身无关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呢?不难发现,它们勾勒了古代希腊人的存在方式或者说他们的世界。正是在他们的世界中,作战才可能被当作一件可称之为作战的事情来加以指认。这提醒我们必须重新检视前面所说的艺术本性在古代思想中的揭示。
重新检视的结果就是,艺术就其本性而言,是通过给出是其所是的事情和物件来让人进入到使这事情和物件得以是其所是的世界。唯其如此,在海德格尔看来,陶壶这一由制陶艺术所给出的物件并不仅仅是一个可供容纳和倾注的物件,毋宁说,透过这把陶壶,“在倾注之赠礼中,以不同的方式逗留着会死的凡人和神祇。在倾注之赠礼中逗留着大地和天空。在倾注之赠礼中同时逗留着大地和天空,神祇和会死的凡人”。在这里,海德格尔用他所考虑的四重整体为我们描述了存在者得以以自身的方式逗留于其中的世界。
在这一点上,较之于哲学家来说,艺术家的方式可能更加直率。马格里特在他所画的一只烟斗下写了一行按语:这不是一只烟斗。这意味着什么呢?是提醒我们这只是画作而非烟斗吗?抑或是想要表明这只是被画出的烟斗而非烟斗本身?画作当然不是烟斗,但是画作必然是有所画的画,因为如果它是无所画的画,那么它就会因为这个无所画而取消作为画的自身,而这意味着绘画艺术本身的取消。在这里,艺术家恐怕是在告诉我们,当艺术以肯定的方式将某样东西交付给我们的同时,它正在以否定的方式将这样东西收回,即把这样东西收回到其是其所是地置身于其中的那个世界,而连同收回的则是取得了这种交付的我们。这样的收回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那个世界原本就是我们置身于其中的世界。
到这里,我们或许可以说,我们获得了关注当代艺术的使命与担当的另外的方式,或者说,本来的方式。作为结果,着眼于当代艺术之审美价值与娱乐价值所做的争论就变得不必要了,况且这样的争论历来充满误解,如果不是说徒劳无益的话。相反,当代艺术毋宁是要让我们获得对于这样一件事情的领会,即,当我们置身于当代艺术的时候,我们既不是审美也不是娱乐,而是以我们自身的方式置身于我们向来所置身于其中的世界。所谓以自身的方式就是指承担责任,而所谓置身于世界之中就是指生活。恐怕只有这样,艺术和生活才不会被破坏。








 吕梁红色经典新年音乐会暨《吕梁山大合
吕梁红色经典新年音乐会暨《吕梁山大合 2023年山西戏剧百事记
2023年山西戏剧百事记 “任跟心名家艺术工作室”揭牌仪式暨传
“任跟心名家艺术工作室”揭牌仪式暨传 大同市2024新年音乐会精彩上演
大同市2024新年音乐会精彩上演 孙业礼任文化和旅游部部长 胡和平不再担
孙业礼任文化和旅游部部长 胡和平不再担

 晋公网安备14010902001572
晋公网安备140109020015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