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现代戏主题创作的三重困境与破局路径
2025-04-16 发表|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沈勇主题创作作为文艺创作的重要形态,本质是以艺术手段回应时代命题。当下戏曲现代戏主题创作却陷入“异化”的怪圈,“三重困境”使其步履维艰。
第一重困境:因主题窄化造成对艺术规律的背离
主题创作的最大困境就是对“主题创作”的误读与窄化。部分创作者将“主题”等同于“政治正确”,将“主题”窄化为政策图解,以“正确性”掩盖艺术表达的贫瘠。如大量的扶贫题材剧目将基层干部的奋斗简化为个人的“开挂式逆袭”,回避贫困群体的生存困境,最终沦为“政策说明书”;有的戏架空现实,将复杂的社会矛盾简化为“反派阻挠—主角逆袭”爽文套路;有的戏将英雄模范塑造成没有亲情、友情与爱情,一心只有事业、毫无瑕疵的“完人”,完全失去“跳一跳够得着”的榜样作用;青年(或曾经的退伍军人)回乡创业,与老村长或父母(或发小)产生矛盾,最后创业成功的套路几乎是当下新农村题材的“标配”……戏曲现代戏本可成为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实现传统艺术现代化的先锋阵地,却因对“主题正确”的过度迎合,陷入“上下左右均不讨巧”的怪圈。更甚者,部分创作单位与团队将“主题正确”视为“护身符”,对批评声以“主流价值观”为由进行压制,从而加剧了观众对主题创作的误读与疏离。这种“自我设限”的创作心态,本质上是将主题窄化为一种单向度的宣传工具。这背后反映出的既是创作主体的“急功近利”,也暴露了创作者创作能力的退化、对现实矛盾的逃避与艺术想象力的匮乏。
戏曲现代戏的题材困境,本质是艺术规律与工具理性的冲突。作为艺术家要摒弃“工具人”思维,要让主题创作回归“人学”本质,要充分体现艺术创作作为复杂创造性精神劳动的特质,强化其从无到有、唯一而无其他的基本品格。
文艺创作是文艺家个体对生活、社会有深刻的感知后,借助自己熟悉的艺术语言的“有感而发”,是一种“不吐不快”的个性化表达。需打破创作中的“唯题材论”,构建主创真正的“体验生活”机制,强化艺术的个性化表达,完善投排剧本“专家审核”、参赛剧本“提升打磨”机制,利用大数据建设题材库与同类题材剧本库,提高优秀剧本价格,大胆起用与培养青年编剧;建立“创作追溯责任制”,建立艺术家专业档案。
第二重困境:因评价体系失衡引发的价值错位
全国每年创作的戏曲剧目在500部左右,而现代戏的占比超过60%,2023年新创的527部剧目中现代戏就达346部。每年都会有很多现代戏获奖。但是,不管在农村的舞台还是在都市的剧场中几乎都难以找到这些戏的身影,偶有演出也往往是为了满足基金或者评奖场次而做的“贴钱赠票”之举,有票房盈利的现代戏几近绝迹,大多数都是“花钱买吆喝”或者“贴钱做政绩”。很多围绕重大时间节点与地域历史文化题材的主题创作,往往是地方政府部门出题目,然后全国招聘高手“承包”或“组队创作”。很多作品都是凭借地方提供的材料而完成“拼装”。但是,因为其符合“主旋律”框架又是地方政府主抓,专家也因其“主题正确”而大力推介。在“功利性”的驱使下,在“获奖”得“政绩”的诱惑下,市场、观众与艺术便被“无视”了。
当专家评审与观众口碑形成两套话语体系,当奖项成为创作的终极目标而非艺术价值的自然延伸,当市场不再是衡量其价值的指标之一,当专家评委也被“主题正确论”绑架,当戏曲现代戏的创作异化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时,戏曲现代戏就从创作与市场的割裂上升到了因评价体系失衡而导致的价值判断“错位”。
“任务式创作”将艺术规律让位于政绩指标,最终既浪费公共资源,又生产大量“泡沫”,不可取;将“思想性”与“市场性”对立,忽视了戏曲作为大众艺术的根本属性,不可取;文艺评价机制过度依赖专家评审和奖项导向,忽视观众反馈与市场检验,也不可取;一味地迎合观众,拿市场票房说话,成为金钱的奴隶,更不可取。重塑评价体系是破局关键。要从“专家垄断”走向“多元共治”。完善评审专家人员结构,组建由行业专家、市场专家与观众代表三方组成的评委库;完善评审办法,让跨地区、跨领域评审成为常态;完善评价体系,建构“评审权、演出权、资助权”分离制衡机制;建立第三方评审委员会,制定评审量化指标,将票房、演出场次、市场反馈与社交媒体热度(影响力)纳入评奖指标,突出艺术性、思想性、市场性、可持续性与可赋能性,打破政绩导向的闭环生态。
第三重困境:因内容贫乏而求助舞台技术的本末倒置
大量的“命题作文”与“急就章”式的写作,让戏曲现代戏套路化表达与概念化讲述成为常态。为在内容的“千篇一律”中找到“新意”与“创新点”,舞台技术成了遮羞布。一些现代戏热衷于斥巨资打造VR舞台与AI互动的“创新”,大量剧目依赖数控升降台、全息投影、LED屏、大转盘等“技术套餐”支撑演出,舞台沦为“伪创新”的赛场和比拼资金的“科技展销会”。
中国戏曲的时空观是诉诸主观的时空观,它弱化了物的因素,强调了人的存在。简约、空旷的舞台,在发挥戏曲诗性的同时,更凸显了戏曲“以演员表演艺术为中心”这一最为核心的特征。事实上,技术堆砌非但未能弥补内容缺陷,反而因成本高昂加剧了资源浪费,这种本末倒置的创作逻辑,不仅消解了戏曲的审美内核,把演员当成了舞台科技的“活体道具”,而且观众通过联想与想象的再创造也被无情剥夺。戏曲现代戏成为了这场“技术竞赛”的最大牺牲品。
黑格尔说:“艺术愈不受物质的束缚,愈现出心灵的活动,也就愈自由,愈高级。”艺术的“减法”往往比“加法”更具挑战性。一方面要给技术加持设门槛,如限制舞美的投入占比,规范技术的增益效果,设定展演剧目装台时间等,防止技术僭越艺术本体价值。另一方面要鼓励戏曲“断舍离”,以空灵舞台再现“描景抒情写人浑然一体”的表演特质。同时尝试设立“艺术科技实验室”等,推动戏曲艺术家与工程师的深度协作。戏曲用六百年证明,好艺术能消化所有新技术,从当年的火把照明到现在的全息投影,只要骨头里的审美不丢,皮囊越新越带劲。
戏曲现代戏的破局,本质是艺术规律对功利主义的宣战。当创作者撕下“主题正确”的标签,当奖项打破“圈内自嗨”的幻觉,当技术回归艺术的“仆人”,戏曲方能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容器。现代戏才能从“政策任务”蜕变为“时代经典”,在传统与现代的激荡中,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戏曲史诗。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









 为蒲剧奉献 为音乐执着 ——蒲剧音乐设
为蒲剧奉献 为音乐执着 ——蒲剧音乐设 舞蹈创作需要提高文学性表达
舞蹈创作需要提高文学性表达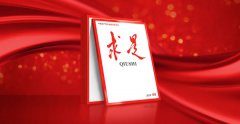 习近平: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习近平: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第十九届中国戏剧节新风向:遏制"大制
第十九届中国戏剧节新风向:遏制"大制 中华文明标识,以艺术“再编码”
中华文明标识,以艺术“再编码”
 晋公网安备14010902001572
晋公网安备140109020015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