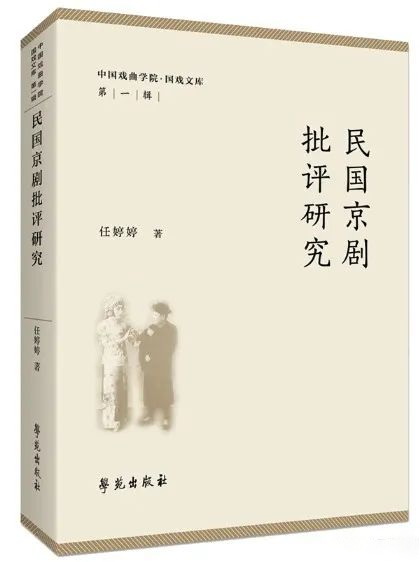
京剧评论写了几十年,现在想起来,对京剧其实还是很隔膜的。因为不了解京剧的内部肌理、艺术特质和独特的表达方式,所以,虽然谈的是京剧,但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叙述语言都不是京剧的。这就像夸一个淑女,却称赞她如何强壮,如何彪悍,总有种张冠李戴的感觉,风马牛不相及也。近几年有所觉悟,特别是读了一些翁偶虹先生的剧评,以为看到了未来努力的方向,但并不容易,有我个人的原因,知识准备缺斤短两,只能望而却步;也有环境使然,毕竟时代不同了,人们对京剧评论的心理期待似乎也有很微妙的变化。总之,京剧评论应该如何写,能够如何写,心里没个准谱。
近日读了任婷婷的《民国京剧批评研究》,对民国京剧批评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跟随她的叙述,民国时期京剧批评的各种形态及演化过程历历在目,依次呈现在读者面前,启发我们重新思考京剧批评写作的问题。此前或有人对清代文人的品花习俗做过研究,而这种研究多限制在文化史、风俗史的范畴之内,很少有人从“京剧批评”的角度对“花谱”的内容做出评价。眼下的这位研究者却通过对“花谱”内容的仔细发掘、梳理,从中发现了一条对伶人的品评及想象从“重色轻艺”到“色艺兼顾”“由色而艺”的转变途径,有了一些可以称之为“批评”的内容,而不再仅仅局限于品评伶人的“色相”之美。
作者谈到她把“花谱”作为研究对象的理由时说:“本书将选择戏曲批评的‘品花’传统作为论述的起点,对民国时期京剧批评范式类型的归纳总结都将从反思和批判这个传统出发。希望借这样一个‘起点’,厘清民国京剧批评追求现代性的线索,并通过这条线索参与建构我们的京剧批评传统,补充民国京剧批评研究的一种路径。”看得出来,作者的叙述始终没有脱离这个研究思路。她从梁启超、王国维、吴梅、齐如山、周贻白、徐凌霄、张厚载等人的批评观念和实践中看到的正是对梨园“花谱”及其余绪异口同声的批评,而民国京剧批评走向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就是对梨园“花谱”中“捧角儿”风气的有力反拨。这也是构建民国京剧批评传统的立脚点和出发点。
从清末到民国,京剧批评一直是努力向上提升的。梁启超、王国维是最早为京剧批评注入新精神、新元素的人,虽然他们选择的方向、路径并不一样,但异曲同工,条条大路通罗马,由于他们的努力,戏曲(京剧)批评开始脱离低级趣味,不仅批评变得严肃,戏曲亦由俗入雅,成为严肃的批评对象。沿着这条路线向前走,京剧的文学性、艺术性、音乐性、载歌载舞的程式和身段等审美范畴陆续进入京剧批评实践的视野。作者有言:“剧评家在反拨旧传统和实现京剧批评现代性的过程中呈现出两种面相:追求批评对象的严肃性和批评态度的批判性。”
侧重固有不同。吴梅侧重“曲”,他是曲学大师,精通音律,如果说梁启超所重视的是戏曲的启蒙教化功能,王国维看重戏曲的文学意味,吴梅则强调戏曲的音乐性,他对京昆的研究,是把“演唱之曲”作为“场上”的重中之重。虽说他的“主要兴趣和研究目标在于读曲、论曲、校曲、藏曲、制曲、唱曲、教曲”,但绝非“与舞台艺术并无太大关系”,但实际上,恰恰由于他的提倡,声腔艺术在京剧中的重要性被凸显出来,其贡献是不容抹杀的。而且,中国古典戏曲的声乐理论由来已久,元代就有燕南芝庵的《唱论》,此后又有魏良辅对昆腔的创造性开发,清代还有徐大椿的《乐府传声》和王德晖、徐沅徵的《顾误录》,这些都表明,在“花谱”之外,还有另一种传统,而吴梅的“曲论”正是这种传统的承续。
作者亦注意到齐如山和周贻白对京剧作为“场上”艺术的研究成果。齐如山将京剧看作是一种“表演的艺术”,虽然他很少对某位演员的表演发表意见,但他系统提出了京剧舞台表演的原理,并概括为“有声必歌,无动不舞”。这种对戏曲本体的认知不仅给民国京剧批评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甚至深刻地影响到当今的京剧批评。而周贻白的研究路径也同样围绕着“场上”而展开。他以“是否能登场”作为评价剧本的重要标准,强调剧本的“可演性”,跳出了以文学性要求剧作的窠臼。他认为,中国戏剧独特的审美品格是由剧场而非文学决定的,这一点至今仍为许多剧评家所认可。
其实,在民国京剧批评传统形成的过程中,剧、戏、伶三者的关系是交织在一起的,作者的研究在这方面是相当充分、细致和深入的,而此后京剧批评范式的建构则非常自觉地继承了这一理论资源。其间徐凌霄与张厚载的批评观念和批评实践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至今仍困扰着许多剧评家。二者的差异集中表现为如何看待剧、戏、伶三者之于京剧的意义。简而言之,徐凌霄试图以“立体文学”调和京剧本体规律与“为人生”的写实主义戏剧理想之间存在的矛盾,而张厚载则以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为中心,围绕演员的唱、念、做、打展开其批评实践,彰显了他对京剧艺术审美特质的理解。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与“为人生”的写实主义戏剧观完全不同的写意戏剧观,更深刻地影响到近百年来的戏剧创作和戏剧批评。王元化先生就曾高度评价张厚载写意戏剧观的历史价值。他将剧、戏、伶三者完全融合在京剧艺术审美的范畴中,为京剧批评建立起一种美学原则。
诚然,作者在研究中是把民国京剧批评中所有评剧、评伶的范式都指向她所谓的京剧批评的历史起点——“花谱”的。而民国京剧批评传统的构建的确与反思、批判、拒绝“花谱”传统分不开。实际上,民国京剧批评并不能回避对伶人舞台表现的描述,毕竟,无论剧或戏,都要依靠伶人展现在舞台上。这里或有“花谱”的“捧角儿”习惯在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又绝不同于“花谱”的“捧角儿”。作者在研究中也注意到,伶人的扮相和面部表情,乃至服饰和脸谱,都不能不纳入京剧批评对象的范畴。很显然,过分强调民国京剧批评传统的建构过程过度排斥“花谱”未必合适,而且,“花谱”也并非清代京剧批评传统的全部,我们前面提到的前人对戏曲音乐性的研究即一例,其间亦不乏对文本、舞台、声腔、程式、身段等元素的研究,这些对后世京剧批评观念和实践,即知与行的影响也是不应忽视的。
(本文作者系北京评协原副主席、北京日报社高级编辑,《民国京剧批评研究》一书获2024北京文艺评论推优优秀著作)

微信扫描二维码,关注山西戏剧网





 晋公网安备14010902001572
晋公网安备140109020015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