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来源不同的题材剧目更加贴近社会多元群体的艺术审美,推动院团形成良性的建设发展机制,出人、出戏、出效益,以更强的内生动力实现传统与现代兼容,创作出真正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艺术作品,这是新时代新的艺术生态对戏曲提出的发展要求。



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戏曲创作优秀案例”,通过遴选在移植改编、整理改编、传承演出、复排提升、跨体裁转化等领域中的优秀创作演出案例,以此倡导“多路径选择、多条腿走路”的创作排演格局,用更多的精品佳作满足时代和人民的审美需求。这无疑是极其有益的举措。
中国戏曲的艺术体系和生态空间突出地彰显了“多样性”的文化立场。三百多个不同个性的剧种、上万个体制机制有别的演出团体,加上戏曲行当的角色分类、演员群体的个性演绎,都让戏曲艺术以最丰富的表达方式,回应着社会多样的审美需求和艺术期待。这也造就了戏曲面对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不同群体时,形成多层次的生态空间和多形态的艺术体系,衍生出各具特色的艺术形态,创造出精彩纷繁的艺术作品,由此决定了戏曲创作演出必然要用多元路径来实现“百花齐放”的艺术局面。
21世纪以来,在社会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戏曲既面对着诸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戏曲振兴工程”等多项利好政策和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文化体制改革”“传承与创新”等整体的发展焦虑。在近年的艺术创作实践中,各地在主题创作、现实题材创作等领域内多有着力;众多戏曲院团亦在原创理念下一味趋新,这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不少剧院团单一化的创作倾向,也遮蔽了很多优秀的艺术实践,造成了戏曲创新实践的困惑。事实上,从21世纪以来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多样化的创作演出机制一直为戏曲的长效发展提供保障:
移植改编是戏曲创作的重要方式,成功的剧目在跨剧种移植改编时,既能保证拥有较好的成功率,又为剧种的再创造、剧目的在地化奠定了基础,越剧《五女拜寿》、晋剧《富贵图》、川剧《马前泼水》、滑稽戏《顾家姆妈》、豫剧《焦裕禄》、蒲剧《山村母亲》、沪剧《挑山女人》、评剧《红高粱》等创作于不同时期的当代力作,至今仍然被其他剧种不断地移植改编;
整理改编是戏曲“三并举”中的重要组成,在浩如烟海的传统剧目库中进行艺术再升华,推陈出新,剔旧更新,让剧目不断臻于经典化。昆曲“青春版”《牡丹亭》、豫剧《程婴救孤》、婺剧《穆桂英》、昆曲《景阳钟》、莆仙戏《踏伞行》、粤剧《白蛇传·情》、湖南花鼓戏《蔡坤山耕田》《夫子正传》、瓯剧《张协状元》、秦腔《潞安州》等众多作品,来源于传统,但却在整理加工后成了真正属于当代的力作;
传承演出是戏曲常态化演出的重要依据,优秀的经典、保留剧目需要常演常新,在代际教学中完成精准传承,在观演互动中实现与时俱化,今天大批的剧种领军艺术家开始逐步进入剧目传承教学,他们曾经传承的前辈艺术经典以及自己创作的优秀力作,通过“名家传戏”工程等传承工作,进入新一代演员的传承中;
复排提升是戏曲推广演出的必要补充,很多精品力作在完成其创作目标后,仍需要进行有效传承和持续推广,以更新的舞台面貌实现创新性发展,京剧《七侠五义》、越剧《红楼梦》、沪剧《雷雨》、黄梅戏《罗帕记》、彩调《刘三姐》、花灯戏《孔雀公主》、藏戏《意卓拉姆》《顿月顿珠》等众多的剧种代表作品,历经几代演员演绎,在复排中实现舞台艺术再次提升;
跨体裁转化是戏曲实现创造性转化的有益探索,在文学、话剧、影视等作品的体裁跨越中,保持既有的文学基础,遵照戏曲艺术规律,形成独具戏曲意蕴的舞台呈现,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川剧《金子》、秦腔《狗儿爷涅槃》《王贵与李香香》、淮剧《小镇》、晋剧《于成龙》、黄梅戏《小乔初嫁》、昆曲《春江花月夜》《世说新语》、滇剧《马克白夫人》、豫剧《朱莉小姐》、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赣剧《李迩王》等诸多作品,从小说、诗歌、电影等体裁中,成功转化为戏曲艺术,为剧种增加了新的精品。
上述在古典剧目、现代题材中不同类型的创作演出方法,实际都具有浓重的原创价值,成功的创演都体现着不可替代的创造性,同时也用多元化的立场,展示了“原创”所具有的开放性,这也成为更加有序、健康的独创得以孕生的促进机制。对于中国戏曲剧种及其代表性院团而言,优秀的艺术实践始终是剧种持续发展的根基所在。让来源不同的题材剧目更加贴近社会多元群体的艺术审美,推动院团形成良性的建设发展机制,出人、出戏、出效益,以更强的内生动力实现传统与现代兼容,创作出真正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艺术作品,这是新时代新的艺术生态对戏曲提出的发展要求。

微信扫描二维码,关注山西戏剧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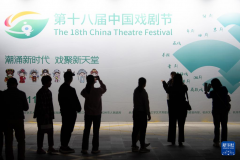



 晋公网安备14010902001572
晋公网安备14010902001572